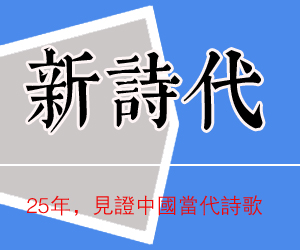提要:本文以诗歌的“声音总体”作为替代“音乐性”的核心概念,涵盖了语调、发音、停顿等语音的物质层面,也包含了语感、风格、文化特性、发声主体等精神性内容,对这些特征的捕获和模仿,才是翻译的关键。由于诗歌的“声音”携带着丰富的文化基因和个人特征,翻译作为对它精准的判断和综合性的把握,实际上也是一次复杂的批评实践。
诗歌翻译之不同于其他诸如叙事类、公文类及科学文献类的翻译,主要在于诗歌文体的殊异。诗歌的表现力极端依赖于它的声音总体性,不惟以韵律为外部形式特点的古典诗歌,以散文化的言语呈现的新诗或现代诗更是如此。新诗的声音总体性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融汇了触发诗歌激情核心的整体语调或语感;体现出诗人情感和沉思断层的分行与分段的口吻、停顿或转折间隙;以及代表着诗人个人特点的选词、句式、句序和特殊符号的各种修辞的声音距离感。一首诗翻译得好与不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原诗总体声音进行传递的效果。
一 理解与转述:原诗声音的再创造
采用“诗的声音总体性”一说,是为了区别于“新诗的音乐性”的传统表述。在自由体诗歌为新诗基本体式的今天,从音乐性的角度探讨诗歌的声音形式已颇难深入,因为当代诗歌不再拘囿于格律的限制,缺少声韵所形成的旋律效果的辅助,诗歌批评家也不可能仅从和谐、流畅、优美等宽泛的言语描述进入对新诗声音的深层规律的考察。当然,这是就整体状况而言,讨论具体的诗歌文本,例如典型的抒情诗时,以局部修辞形式出现的韵式也还存在,但那也基本服务于一首诗总体的声音特质。在阅读自由体诗歌的时候,普通读者(或对现代诗歌缺乏感知训练的读者)往往因捕捉不到诗歌之所以成为诗歌的因素,而要么期待诗歌的语言具有辞藻优美或华丽的“诗意”,要么依赖于听觉上能体现诗人在激情驱使下的情绪强度。我们总是听到来自一些读者对新诗的抱怨:“这也是诗吗?”不仅因为他们的参照标准(也是阅读口味)经常是格律严整、声韵规范的古典诗歌、新格律体的抒情诗等,而且也因为他们的诗歌听觉并没有得到感性上的开发。一般来说,诗歌读者的阅读趣味概由既有的诗歌观念和新增的阅读经验混合形成,如果经常阅读某一类型或某种风格的诗歌,由此形成相应的诗歌观或审美观并逐渐固化,一个人的耳朵就会像被关闭了一样,逐步失去对新的声音样态的敏感。加之,新诗中业已缺失了吟诵传统,使得我们今天的诗歌阅读方式更偏重目读,即让诗行悄然溜入大脑,并在头脑中形成一个笼统的声音形态。目读(或视觉性的阅读)对于声音接受需要一层想象的声音“翻译”,即需借助想象,领会词语和句子背后诗人的情绪变化,音调起伏,以及心绪、感情、想象和思考综合而成的总体的声音特质。又因目读的速度一般偏快,很难抓住微妙变化的声音细节,若非反复研读或如研究者般地精读,一首诗的声音很容易如轻风过耳一般被读者忽略。
在《如何读诗》一书中,英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这样定义诗:“诗是虚构的、语言上有创造性的、道德的陈述,在诗中,是作者,而不是印刷者或文字处理机决定诗行应该在何处结束”[1]。后半句强调在何处结束诗行,即联系着对诗的声音的理解。“诗行的结束”即分行、分节和诗的结尾,与诗人的呼吸感,使用言语的强度和情绪的丰富性直接相关,与其他文类比较,正是“诗行在何处结束”这个特点决定了诗歌的文体特质。基于此,准确地把握原诗包括言语风格质地和修辞细部在内的总体声音,就是诗歌翻译中要处理的主要工作。一般而言,诗歌翻译的从事者需要相当高水平的外语(原诗的语言)能力,但我们也经常听到一种说法,认为只有译者的母语表达力相当高才能译得好,比如说他/她最好也是一位诗人,原因大约正在于此。因为显然,诗人较一般读者更具有敏锐的语言听觉力。
对诗歌表达中声音的敏感,而不仅是意义的掌握,相对而言需要较强的语言理解与转述能力,如何将这种理解与转述在翻译的目标语言(即译者的母语)中实现,就使得诗歌翻译工作带有了再创造的性质。特别是再创造原诗的声音,因为在翻译成的目标语言中,如何断句分行,分节和结尾停顿,是不可能也不必与原语言完全一致的。过度和刻意追求与原诗词序、分行的一致,很可能导致译文的生硬与呆板。除非原诗的诗句内部有明确的强调部分,在译文中可以且应该得到体现。作为一首诗的两个版本(原本和译本),译本要遵从原本总体的声音设定,即需要从词句的层面了解到音高、语速、停顿、口吻和语调,更重要的是,需要知晓形成这一切的背后的表达情绪状态和心理动机,诗人的个性和品格。
举一个讨论翻译的例子,在引用了洛威尔(美国诗人)翻译的拉辛诗剧《费德尔》中的一节后,乔治•斯坦纳批评道:“这几行台词精确地为他(希波吕托斯)在戏剧中复杂的情感纠葛‘定位’,表现出他的正直但羞怯随和的美德。在洛威尔雄辩的声音中,这些特点丝毫没有得到暗示。”在乔治•斯坦纳看来,洛威尔以译文“雄辩的声音”歪曲了原诗“茫然与犹疑”的“基调”,丢失了原诗中折射希波吕托斯性格的“神秘而微妙的语感”[2]。在这里,“基调”、“语感”是原诗中的声音元素,是诗人通过语言的表达“暗示”出来的,需要通过翻译在目标语言中得到再现。然而,这种再现无法仅从原诗言语表层捕捉,而要首先在原文里领会声音之发生的根据,即希波吕托斯“茫然和犹疑”的性格,这种领会跳出了诗歌语言的物质声音层面,是理解诗人之所以如此写作的生发点,只有经过这一层理解之后,才可能在目标语言中找到传达“茫然与犹疑”之语感的词语和节奏。美国当代诗人、翻译家乔治•欧康奈尔曾经描述过翻译中译者如何体会原诗声音发生的根据,他说:“我认为成功的翻译是译者探索发现自己曾经处于他(她)认为的、感觉的或想象的原诗诗人所处的地方,这个地方位于语言之前”[3]。言下之意,译者所扮演的角色实则是研究者加诗人,他(她)需要经过原诗回溯到原诗被创作出来之前的空间位置所在,然后如同诗人一样,在目标语言里复写出那首诗。如何恰当准确地译好《费德尔》?按照乔治•欧康奈尔的提法,洛威尔应先成为拉辛,再写出希波吕托斯,而不是在译文中让希波吕托斯成为洛威尔自己。
概而言之,诗歌翻译是在对原诗充分理解的前提下,对其声音总体性在目标语言中的转述或重述。这样的翻译理念并不拘泥于两种语言中词语的对等性,也不刻意追求或制造对应于原诗的音韵、格律和诗体形态,而更侧重于实现目标语言中诗歌言语层面的新鲜质感,以使原诗的第二生命焕发并增殖。这样,诗歌的翻译也可以称得上是一种诗歌的再创作。
二 拆散与重塑:测听诗歌声音的多重性
乔治•欧康奈尔提到的那个位置,即“位于语言之前”的“原诗诗人所处的地方”,向译者和读者提示了两条理解线索,一,诗人与诗的表述者(“抒情主人公”)并非同一个人,诗歌的声音由二者共同塑造,并主要由后者体现;二,挑战一个译者的不仅是他/她的外语能力,而且更是他/她的文学理解力和母语表达能力,极而言之,译者翻译的不是一首首诗,而是那个诗人及其创造的声音主体。译者要拥有成为那个被译的诗人的意识,抑或,在声音感受与传达方面,译者要如同一个模仿能力高超的,懂得忘我的演员一般,扮演那位诗人,在译文中做到绘声绘色、生动而传神,以重塑那位诗人笔下的诗歌主体(角色)。相较于一般性的阅读,翻译对理解诗歌声音总体性的要求更高,翻译也凸显了诗歌声音的复杂性和多重性。关于第一点,“诗歌主体”与“经验自我”的分离,是自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兰波以来现代抒情诗的重要特点之一[4]。它从阅读上要求现代读者转变阅读期待,禁止人们将现代抒情诗理解为诗人的传记式表达。换言之,在现代抒情诗中,诗歌的发言者并非诗人,而是由诗人创造出的诗歌主体,诗歌的声音并非由诗人的经验自我发出,而是虚构自我在发声。区分这两种声源对于译者有什么意义呢?结合这里所说的第二点,翻译要成为那个诗人,进而也成为那个诗人创造出的声音主体,意味着译者也应通过翻译区分出两种声源,将“诗歌主体”与“经验自我”分离,同时,在译文中重塑原诗的诗歌主体,赋予它在目标语言中新的生命(也即新的声音)。这是一种拆散与重塑的工作,体现了现代诗歌声音的多重性。
诗歌主体的虚构特征要求译者不能仅将诗歌的声音还原为他/她理解中的原诗诗人的声音(但可能诗人的声音依然是一种参照),那么,作为译者,他/她应能(或可能)测听到一首诗的声音层面包括哪些呢?由于我们阅读现代诗歌多数时候是以目读的方式,诗歌的声音需要借助想象转换才能得到具体、细致的呈现。让我们回到特里•伊格尔顿对诗的定义,在强调诗之为诗的声音特征——即何处结束诗行的重要性之外,他还提出诗是一种“陈述”(statement)。陈述更接近于谈话,而非抒发,这提示了现代自由体诗歌的总体语感特征,那就是它总是与来自生活现实中的交流语调相关,无论是侧重口语风的,还是偏向书面语式的。一首诗的总体语调联系着写作者的心情和心性状态,或是严肃的、一本正经的,或是机智诙谐的,抑或是反讽的,当然也有我们能很快辨认出的,如慷慨激昂的,深情款款或缠绵悱恻的。在阅读和翻译一首现代自由体诗时,首先需要确认的就是诗的语调。不同的语调可能指向不同的诗歌主题,但更常见的现象是,同一个主题可以由不同的语调书写。一首诗的语调可以不单纯或单一,但具有整体上的统一性。总体语调之下,是诗人对主题展开和内容书写过程中所体现的声音的丰富复杂特征,在形式上呈现为节奏的多变。再者,一个译者如能听取诗句背后的隐含的声音质地,即弦外之音,他/她便能达到完整、全面地把握诗歌的声音特征了。
强调听取诗歌总体声音特征的重要性,并不是说在翻译中准确地译出诗歌所传达的意义(意思)是次要的,而是说传达意义相对并不那么难以做到。在讨论诗歌翻译时,王佐良指出,相较于传统形式的英语诗歌,自惠特曼-威廉姆斯一路的20世纪中期以来的典型的“美国诗”则颇为“难译”,而“所谓难,不在于人们常说的‘形似’。光从这路诗的表面意义讲,用汉语传达并不难。在这种水平上,还有比威廉斯的《一架红色手推车》更容易翻译的诗么?然而译出了它的全部词的字典意义,完全照原作断行,保存了所有的形象,并不等于译出了这首诗,因为缺了原有的节奏,口气,回响,言外之意,而这构成了诗的意义的一部分。这种节奏、口气、回响、言外之意又是美国现代生活里产生的,是美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分”[5]。确如王佐良所言,诗歌的声音特征也是其意义的组成部分,而译出这一部分恰恰最需要汉语的感受力与创造力。王佐良关于诗歌翻译的实践与研究富有启发性,虽未提出关于诗歌的声音特征的概念或表述,但他通过对卞之琳的莎士比亚翻译的研究,切实地探讨了译诗中的声音议题。王佐良认为,除了探讨原诗为格律体,译诗以“顿”(音节)组合对应原诗音步,并依原诗押韵,从而成为“相当于原作”的翻译实践之外,对于既是诗又是剧的舞台语言(如莎士比亚“无韵白体诗”),卞之琳能够重视其语言作为“传达工具的任务”之外的“额外的戏剧作用”,如理解哈姆雷特时,“通过对语言的感应来突出主人公的知识分子性格”的特点[6]。而“对语言的感应”恰恰指的是译者能听出原诗中体现了说话者的口吻、语气、声调、音高、语速、情绪和体现了言外之意的戏谑、反讽等的声音元素,并通过选词、节奏和相应的句子长度、密度等译现出来。从翻译的方法看,这其中就包括了一种阅读的拆解与译写的重塑的过程。
相较于其他文类的翻译,翻译诗歌还存在一些理解与接受的习惯性误区,比如不自觉地强调诗歌语言的优美,词句意思的准确,以及译文的通顺等。对于译诗的类似要求来自部分读者,也来自部分译者。对于一些译者来说,“信、达、雅”是被他们反复引用并加以发挥的另一种说法。“信”即准确,“达”为通顺,“雅”是优美,这是严复当年对“译事”提出的三个标准,而用在今时对待新诗的翻译已显得过于粗略和简单。如上文所述,这些偏见误识一方面与固化了的诗歌观念有关,同时也是由于听不懂原诗的声音所致。懂与不懂原诗的声音,并非指具体的词句发音及意义理解,而是指弥漫在词语发音这种物质声响之中的涵义指向。一个“啊”字,可以有至少八种以上不同的意指,根据它的不同声调,长短、节奏变化、重复与否以及在句子中的位置等决定。
测听原诗的声音因素(总体语调、音高、语速、节奏、语感、口吻等),在翻译实践中都应视原诗的具体情况而定。艾米莉·狄金森本来在英语中就是一个很难读的诗人,她经常遣用有歧义的词,句子之间因诗人想象力的奇崛而呈现的跳跃性,诗歌内部远距离的呼应等,这些如果在翻译中因强调译文的可解性而被加工处理并抹平的话,往往就会使得汉语中的狄金森失去了她在英语文学中的原创性和独特性。在汉语的译介中,西尔维娅·普拉斯一些诗句的直接、大胆与极致表达,甚至使得不同的汉译本出现了奇特的接受处境,有时候,不太准确、硬伤累累的译本反而可能在表现普拉斯写作独特性的方面优于那些原文意义传达准确但遣词更重和声音传达平稳的译文。这种现象在诗歌翻译中即便算不上特殊,也是经常能碰到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在整体上理解一位诗人的诗歌总貌,而非仅强化其风格特征,何况个人风格的形成也离不开一个诗人对诗歌传统与历史性的继承与创造。
 在线投稿
在线投稿 手机版
手机版 | 诗品文库频道
| 诗品文库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