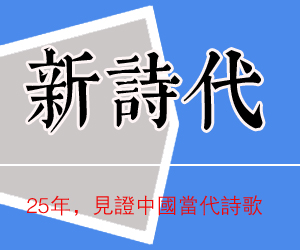三 批评视角中诗歌的“声音”与“形式”
在翻译中,如何传递原诗的声音,部分地关乎如何译出诗歌的原创性。此处的原创性,指的是诗人在自己的诗歌和文学传统中所体现的独具开创性的语言风格特征,亦即他/她的诗歌所具有的独特的声音总体性。一首诗能体现诗人的整体风格及其原创性,一位诗人是否具有原创性既是相对于其自身的文学史,也是相对于全部人类的诗歌史而言的。他/她通过自己的写作增添与改写了既有的文学历史格局。从翻译的角度看,如果我们认为波德莱尔、兰波、瓦雷里具有原创性,那么,汉语的译文如何呈现这种法语文学传统中的突变与提升呢?仅仅在现代主义、象征主义这样的文化思潮和艺术观念的向度加以讨论有可能是不够的。同样,俄语中的曼德尔斯塔姆、茨维塔耶娃、马雅可夫斯基,西语中的洛尔迦,德语中的策兰又如何呢?译者不仅要有世界文学的视野和不同语种的诗歌艺术的知识储备,还需要有对具体诗人的声音独特性和语言个性的理解。译者的总体修养决定了他/她的诗歌译文的质量与可读性,这也是有时候转译的诗反而比直接从原语言翻译的诗歌更吸引人的原因。因为即便是转译,如果在不同语言的转换中,原诗的声音得以准确的传递,那么,转译的译文也能保留原诗最初的言语质感与整体风格,乃至诗人的原创性。
从这一意义上讲,翻译即批评。一位译者应能辨识原诗的所有要素也是一位批评家能够辨识的。由此,我们更信任那些在翻译过程中做过大量准备的译者,为了翻译好一首诗,他们不仅通读并尽量精确地理解它的内容,而且,还沿着原作者和诗作本身的路线,去钩沉诗人的生活、诗歌形式的流变等要素,力争在一首诗的翻译中熟悉一位诗人和一个特定的诗歌传统,甚至进而有能力对这首诗和这个诗人作出公正的评价。
引入批评的视角,也因为在职业或学科意义上的诗歌批评中,“声音”经常被作为文学形式的因素之一而得到讨论。在《如何读诗》的“寻求形式”一章中,特里·伊格尔顿讨论了形式和内容二分法的复杂性与必要性,他指出诗中的一些要素并不能够完全独立于内容来理解,比如情调、语调、音高、反讽、隐喻或含混等,而我认为这些因素通常与一首诗的声音总体特征相关。即使没有直接以声音为批评概念——而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诗歌毕竟不是音乐,不是纯声音形式,在中国新诗批评史上,我们也可以经常看到对于诗歌声音的讨论,特别是在具体地讨论节奏、格律和风格的音乐性等的批评文章中。贯穿新诗批评史中的自由体和新格律体两种构想的批评话语,也使得新诗的声音批评话语更其扭结复杂。新格律诗的倡导者、新月诗人、批评家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一文开篇就以下棋为喻,斩钉截铁地论到“棋不能废除规矩,诗也就不能废除格律”。有趣的是,他是在翻译的视野中解释“格律”的,他说:“格律在这里是form的意思。‘格律’两个字最近含着了一点坏的意思;但是直译form为形体或格式也不妥当。并且我们若是想起form和节奏是一种东西,便觉得form译作格律是没有什么不妥的了”。严格意义上,格律对应的英文词汇是metre,而form则是指涵义宽泛的“形式”。虽然我也赞同在概念的翻译上可以不必拘泥于辞典意义上的对应性,但闻一多将form译作格律还是带有强烈的个人性。新格律体的主张和实践的成败并非本文的论述重点,但作为新诗创制早期的作者,闻一多对新诗形式进行总体设计,应是他提出“格律说”的初衷。为了强调他所认为的新诗体式的重要性,他既将form(形式)解说为“格律”,又把这个格律等同于“节奏”,进而他根据格律的两种类型(“属于视觉方面”和“属于听觉方面的”)推演出新诗的“三美”说(即“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以及“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7]。尽管通过与古典诗歌中的“律诗”的对照,闻一多认为新诗的格式“是根据内容的精神制造成的”,“可以由我们自己的意匠来随时构造”,但他的新诗体式的总构想仍然是要赋予它一个类似中国古典诗歌的,相对确定的形式来。换言之,他不赞成“自由体”的新诗。而显然在观念上与之相对的废名,则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新诗应该是自由诗”的见解。废名也选择了与旧体诗比较来讨论新诗的方向,他也采取了比拟法,认为旧诗的内容是散文的,其文字(形式)是诗的,而新诗的内容是诗的,文字(形式)则是散文的[8]。这一著名而笼统的观点或许会引发理解上的歧义或争议,但废名也依然是在新诗何以成立的前提下思考这个课题,即在“诗体解放”的同时又如何保持“诗的感觉” 与当时的批评家、诗人胡适、闻一多所持新诗观点辩驳,通过对新诗草创期不成熟的作品的批评以及对古诗中温庭筠、李商隐一脉诗作的解读,废名进一步阐发了他的观点。有关新诗的内容如何是诗的,我且不展开引述废名的看法,只说他也未曾深入的“文字是散文的”部分。废名说:“在新诗的途径上只管抓着格律的问题不放手,我以为正是张皇心理的表现,我们只是一句话,白话新诗是用散文的文字自由写诗。所谓散文的文字,便是说新诗里要是散文的句子”。“我们的白话新诗是要用我们自己的散文句子写。白话新诗不是图案要读者看的,是诗给读者读的。新诗能够使读者读之觉得好,然后普遍与个性二事俱全,才是白话新诗的成功”[9]。与闻一多略显机械的格律体式设计思路相比,废名对于新诗的诗性内容的强调更切近现代诗的内核,但简单地以“散文的句子”来理解新诗的形式则颇浅略,并且它针对的是旧体诗的句法陈规,却没有对新诗采用的散文的句子到底有怎样的形式特征,何以可以与诗性内容协调作出更具体、细致的论述。或许,引入“声音”概念探讨新诗语言形式(句子的特征以及格律问题)不失为一个有包容性的新视点。因为“声音”既可以包括传统诗学概念中可具体分析的诸种形式要素,比如音节、语调、音高、节奏等,也可以与更具语义内涵的反讽、讽刺等手法结合理解,还能以其运用语言的规律性而与韵律、格律等诗歌特质相关联。
当代一些活跃的诗人、批评家已经开始注意到现代诗歌的声音问题,西渡、张桃洲、陈太胜、翟月琴等,撰写过论文、论著,或从新诗合法性问题切入,或以声音研究诗人诗作等,对现代诗歌中的声音特征、声音与韵律的关系等问题展开研究。本文只从诗歌翻译的实践和经验出发,考察如何在翻译行为中把握与传递原诗的声音特质。总之,翻译是一种变形,是诗歌身体的増变和声音总体性的传递。在有关诗歌翻译的表述中,我们也常听到如下两种典型的表达:“诗歌是不可译的”,“诗歌就是翻译中丢失的部分”。“不可译的”和“丢失”的那部分到底指的是哪些因素?一个基本的看法是诗歌的声音元素。比如原诗语言中的格律音韵,不能够被完全移译过来,这是翻译中令人遗憾的方面。《山海经》中的著名的“精卫填海”神话故事,可以用来作为诗歌翻译的一个隐喻。炎帝之女女娃溺海而亡,由之激发出的生命抗争意志使她化身为小鸟精卫,衔着微小的事物树枝、石子等,发誓填平大海。精卫的名字是根据小鸟啼叫的声音而来,它也是女娃生命意志的传达。而诗歌的译者也正是“精神的守卫者”,或即翻译中生命之声的传递者。
注释:
[1] [英]特里·伊格尔顿:《如何读诗》,陈太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11月,第32页。
[2] 《两种翻译》(1961),参见[美]乔治•斯坦纳:《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李小均译,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11月,第245页。
[3] 《对中国当代诗歌的翻译》,参见孙晓娅编撰《彼岸之观:跨语际诗歌交流》,第27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1月。
[4] 参见[德]胡戈•弗里德里希著,李双志译《现代诗歌的结构: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的抒情诗》第三章《兰波》中“虚构的自我:去人性化”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兰波作为象征主义诗人的代表,其诗歌主体的虚构性,是对既往的(包括浪漫主义)诗歌的抒情主体与诗人合一特征的超越,同时也开启了现代诗歌主体与经验自我分离的先河。换言之,现代以来的抒情诗歌主体均带有了某种象征色彩。
[5] 王佐良:《汉语译者与美国诗风》,收入王佐良著《论诗的翻译》,第97-98页,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8月。
[6] 王佐良:《一个莎剧翻译家的历程》,收入王佐良著《论诗的翻译》,第34-49页,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8月。
[7] 闻一多:《诗的格律》,参见《闻一多全集》第二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8] 废名:《新诗答问》,参见陈均编《新诗讲稿》(废名、朱英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3月版。
[9] 废名:《已往的诗文学与新诗》,参见陈均编《新诗讲稿》(废名、朱英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3月版。
来源:本文原刊于《文艺争鸣》2019年第2期
 在线投稿
在线投稿 手机版
手机版 | 诗品文库频道
| 诗品文库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