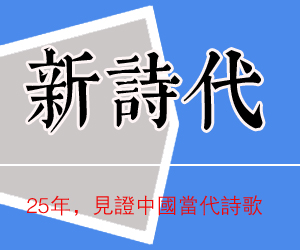约翰·阿什贝利(John Ashbery,1927-2017)阿什贝利生于纽约州罗切斯特,在安大略湖附近的一所农庄长大;童年时曾失去了一个弟弟。阿什贝利在迪尔菲尔德学院接受了教育。迪尔菲尔德是一所全男性的学院,阿什贝利在那儿读了威斯坦·休·奥登和狄兰·托马斯的诗歌,并开始写诗。1949年从哈佛毕业,他写了关于奥登诗歌的论文。阿什贝利曾在纽约大学短暂学习,195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拿到硕士学位。1970年代早期,阿什贝利开始在布鲁克林学院任教。1983年他被选为美国艺术及科学院会员。1980年他迁往巴德学院。在那儿担任小Charles P. Stevenson语言文学教授,2008年退休。2001至2003年他是纽约州诗歌奖得主,并任美国诗人学会秘书多年。他还是卫斯理大学Millet写作学会会员。他与伴侣大卫·凯尔马尼住在纽约和哈德逊。2017年9月3日,阿什贝利于纽约州哈德逊的自宅中安详辞世,享耆寿90岁。
约翰·阿什贝利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美国诗人之一。他几乎赢得了美国诗歌奖的所有主要奖项,包括普利策奖、国家图书奖、耶鲁青年诗人奖、布林根奖、露丝·莉莉诗歌奖、格里芬国际奖和麦克阿瑟“天才”助学金。Ashbery的诗歌要求读者放弃关于诗歌的目标、主题和文体的所有假设,转而选择反映语言极限和意识波动性的文学。2008年,评论家兰登·哈默(Langdon Hammer)评论道:“在过去的50年里,美国诗歌中,没有比约翰·阿什贝利这样重要。”
一部长篇小说
他的罪行会变成什么,既然她的手
已坠入睡眠?他收集事迹
在纯净的空气中,它们实际上
过剩的媒介。她一吸气他就笑。
如果它在开始之前
便已结束——这悲哀,这雪
坠下,坠下它美丽的遗憾。
爱神木在他慷慨的眉毛边干燥。
他比日子还要宁静地站立,一种呼吸
在其中所有的罪都是同一种罪。
他是最纯净的空气。但她的耐心,
必不可少。变得,颤抖
从前双手在那里。在发臭的空气中
每片雪花都仿佛一个皮拉内西
在过去中坠落;他的话
因最终的含义而沉重。夫人!含羞草!所以
结局是一样的:不负责的唾沫
喷入结冻的空气。除了那个,在一片
滑稽的新风景中,没有音乐,
用音乐书写,他知道他是个圣人,
当她触摸所有的善
像触摸金发,知道它的善
是不可能的,醒来,醒来
当它在爱人的眼中生长。
这些湖畔城
这些湖畔城,从诅咒中长出,
变成善忘的东西,虽然对历史有气。
它们是这个概念的产物;比如说,人是可伯的。
虽然这只是一例。
它们出现了,直至一个指挥塔
控制着天空,用巧妙浸入过去
寻找天鹅和烛尖似的树的枝条
燃烧着,直到一切仇恨者变成无能的爱。
那时你留下来陪伴自己的意念
还有午后愈来愈强烈的空虚感
它必须被发泄向别人的窘迫
那些人象灯塔样飞过你的身边
夜是一个站岗的哨兵
你的时间至今多半用来玩创造性的游戏
但我们有一个为你拟好的全面计划
譬如说我们想把你送到沙漠的小心,
或者狂暴的大海,或将他人的接近作为际的空气,
将你压回一场惊醒了的梦,
好象海风抚摸着孩子的脸。
但“过去”已经在这里,你在孵育自己的计划。
最坏的情况还没有结束,但我知道
你在这里会幸福的,这因为你的处境
的逻辑可不是什么气候能耍弄的
有时温柔、有时飘逸,对吧。
你建立了一座山样的建筑物,
沉思地将你全部精力倾注入这纪念碑
它的风是使花瓣硬朗的欲望
它的失望喷发成泪水的长虹。
街头音乐家
一个死了,另一个活着,他的
灵魂被生生地拧走,踟蹰街头
穿着自己的“身分”象裹着件大衣,
日复一日同样的街头,油量表、阴影
在树下。比任何人被召唤向更远的地方
穿过日益增加的郊区风度和举止,当秋色落向
豪华的落叶,推车里的破烂
属于一个无名的家族,被排挤到
昨天和今天这步田地。一个瞪着眼
瞧另一个打算干什么,终于露了馅,
于是他们彼此相仇视,又相遗忘。
所以,我摇着、抚慰着这只普通的堤琴,
它只知道那些人们忘记了的流行曲调
但坚持它能将一段无味的叠句
自由发挥。十一月里这一年翻转着身子
日子间的空隙更明确,
骨头上的肉更明显。
我们关于根的地方何在的问题
象烟雾样飘悬:我们如何在松林野餐,
在岩洞中,有流水不断地渗出
留下我们的垃圾、精子、粪便,
到处都是,污染了风景。造成我们可能达到的模样。
焦虑问题
五个年头过去了,
自打我开始生活在我正在对你们讲的
那些阴暗的小城。
是的,没有多少变化。我仍说不清
从邮局出来怎样才能走到公园的的秋千边上,
苹果树凌寒开花,并非出于什么信念。
我的头发嘛,是药蒲公英茸毛的颜色。
想一下这首诗讲的就是你,
你能填上我小心省去的内容吗:
要写写痛苦,性,以及人们互相之间
怎样诡秘地行事?不是这些,它们似乎
在一些书里全有了。对你
我省去了讲述手指三明治,
以及那来自青铜壁炉的眼镜后的目光,
它惊诧地盯着我,永远不会缓过来了。
 在线投稿
在线投稿 手机版
手机版 | 诗歌翻译频道
| 诗歌翻译频道